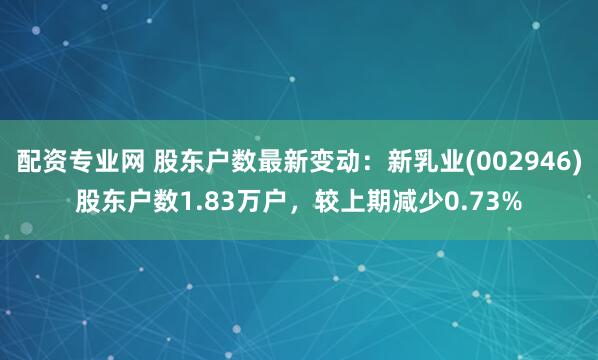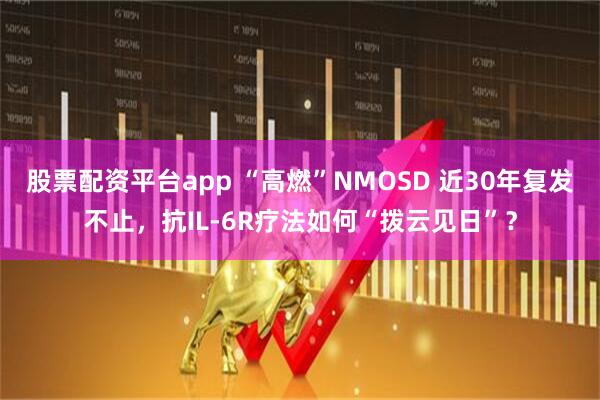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股票配资平台app
3种序贯药物治疗后仍复发,NMOSD患者治疗还有哪些转机?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s, NMOSD) 多以严重的视神经炎和纵向延伸的长节段横贯性脊髓炎(longitudinally extensive transverse myelitis,LETM)为主要临床特征[1]。据统计,约60%的NMOSD患者在症状出现的第1年内复发,超过90%的患者在3年内复发,导致患者丧失行动能力或失明,因此预防复发治疗对于NMOSD患者至关重要[2]。
本期将分享一例以视神经炎急性起病、随后近30年间反复复发视神经炎或横贯性脊髓炎的51岁女性NMOSD患者诊治经历。患者前期病程中由于未接受规律治疗,病情持续进展导致双眼近乎失明、双下肢麻木无力;病程后期患者在接受利妥昔单抗、吗替麦考酚酯以及伊奈利珠单抗这3种序贯治疗药物后仍反复发作,直至转换为萨特利珠单抗治疗后病情趋于稳定,且治疗期间未出现明显感染或其他不良反应。
病例介绍
基本信息:患者女,51岁。
主诉:反复视力下降伴双下肢麻木无力28年,加重1月余。
现病史:
1992年~2020年:1992年首次以视神经炎发作起病,之后反复复发视神经炎/脊髓炎,平均1年2次,缓解期予以口服激素或联合硫唑嘌呤治疗,但因副作用停用,遗留双眼视力极差、季肋部疼痛等症状。
2020年7月:突发双下肢麻木无力、不能行走,考虑脊髓炎复发予以甲泼尼龙500mg+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5天,后口服激素序贯治疗。2020年8月:患者为求进一步诊治入院。
入院神经系统查体:右眼失明,左眼仅有光感,左下肢肌力4-级,右下肢肌力5-级,双下肢痛、触觉减退,双侧病理征阳性。
实验室检查示:AQP4抗体84.29 U/ml,CD19+B细胞百分比25.46%。
入院后完善乙肝、结核、肿瘤筛查后予以启用利妥昔单抗序贯治疗。
后续序贯治疗:
利妥昔单抗:用药后复发两次
2020年10月24日,患者第一次接受利妥昔单抗100mg+500mg静脉滴注,但未按要求规律监测B细胞,2021年8月24日脊髓炎复发,在当地医院接受甲泼尼龙500mg冲击治疗。2021年9月27日,患者第二次接受利妥昔单抗100mg+500mg静脉滴注,2022年2月11日患者B细胞较前明显升高,AQP4抗体57.81 U/ml,患者因药物耐受问题(用药后头晕、乏力)拒绝再次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2022年6月11日患者双下肢无力麻木症状加重,MRI提示T1-6脊髓异常强化灶,考虑脊髓炎复发。
吗替麦考酚酯:用药后复发一次
2022年7月1日患者开始口服吗替麦考酚酯预防复发,2023年4月17日患者再次出现双下肢无力麻木加重,MRI提示T2-8脊髓异常强化灶,考虑脊髓炎复发,当地医院甲泼尼龙冲击治疗5天后改为口服激素序贯治疗。
伊奈利珠单抗:用药后复发一次
2023年6月13日及28日分别予以伊奈利珠单抗治疗,后续多次复查B细胞水平维持在0,但患者仍于2023年12月6日出现右上肢麻木,12月9日出现右侧颈部麻木,MRI提示颈髓强化病灶(图1),急性期治疗后出现神经病理性疼痛后予以对症治疗。

图1 患者接受伊奈利珠单抗治疗后复发时脊髓MRI
(A图:T2WI;B图:T1WI增强显示颈髓强化病灶)
萨特利珠单抗:用药后病情稳定
2024年2月7日,实验室检查示患者血清AQP4抗体滴度显著升高(1:1000),为预防复发及残疾症状进一步加重,2月10日接受萨特利珠单抗第一次注射治疗,后续按首月3针后每四周1针持续治疗至2025年5月,病情稳定,无明显感染及不良反应。
治疗期间复查:
实验室检测:2025年3月26日血清AQP4抗体滴度1:1000(CBA法);B淋巴细胞7.95%(参考值:6.45%~18.9%),CD20+B细胞7.88%(参考值6.35%~18.97%),CD27+记忆性B细胞1.4%↓,T细胞及NK细胞均在正常范围内。
影像学病灶:2024年9月2日复查颈椎MRI示颈髓内异常信号较2023年12月9日缩小,增强后未见明显异常强化;2024年12月31日,C2-C3层面颈髓内异常信号较2024年9月2日进一步缩小,增强后未见明显异常强化,T1-6层面胸髓内异常信号较前相仿。
本病例详细介绍了一位51岁女性患者的治疗经过。患者以视神经炎起病,早期因治疗不规范,视神经炎/脊髓炎反复复发近30年,双眼几近失明。2020年起患者开始接受利妥昔单抗序贯治疗后出现2次复发,转换为吗替麦考酚酯治疗9个月后再次复发,转换为伊奈利珠单抗治疗后虽B细胞维持在0,但5个多月后又出现复发,遂转换为萨特利珠单抗序贯治疗,治疗15个月期间患者病情稳定,脊髓病灶范围及强化程度明显改善。
伊奈利珠单抗是一种人源化的IgG1亚型CD19单克隆抗体,可导致表达CD19的B细胞耗竭[1]。本例患者前期多种免疫治疗失败后转换为伊奈利珠单抗治疗后实现了B细胞耗竭,但AQP4抗体滴度仍然较高(1:1000)并出现复发,这或许与长寿命浆细胞有关。长寿命浆细胞之所以能长期存活,不仅因为这些细胞表面不表达CD19和CD20,也与其持续接触微环境中的存活信号因子[包括细胞因子、黏附分子、转录调节子和凋亡调节因子,如B细胞活化因子(BAFF)、增殖诱导配体(APRIL)、白细胞介素-6(IL-6)等]有关[3]。因此,作用于CD19+/CD20+B细胞的B细胞耗竭剂无法清除长寿命浆细胞,这也是本例患者接受伊奈利珠单抗治疗后仍出现复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存活信号因子中,IL-6不仅可诱导浆母细胞分化,维持浆母细胞的存活与功能,还可促进长寿浆细胞长期存活及分泌致病性抗体[4-5],这为靶向治疗提供了重要方向。研究显示,使用IL-6R抑制剂可显著减少CD19+和CD19-抗体分泌细胞[6],从而有效抑制长寿命浆细胞驱动的持续性自身免疫性炎症。萨特利珠单抗作为一种抗IL-6R单克隆抗体,作用机制明确,以高亲和力全面结合IL-6膜结合受体与可溶性受体,且经SMART抗体工艺技术改造后还能多次与靶点结合,延长血浆半衰期约30天,有效减少了药物给药频率与剂量,且其皮下生物吸收利用度高[7]。本例患者转换为萨特利珠单抗治疗后未再复发,提示萨特利珠单抗或可有效抑制长寿命浆细胞的活性。
此外,本例患者接受萨特利珠单抗治疗后,MRI显示颈髓病灶范围缩小且无强化,这与IL-6R抑制剂强大的抗炎作用密切相关。NMOSD的致病过程可被视为一种从外周到中枢全线“失控”的广泛性炎症级联反应,包括外周T细胞向Th17细胞的异常分化后导致IL-6、IL-21等炎症因子异常大量释放,不仅诱导致病性T细胞的分化增殖,同时促进祖B细胞分化为致病性浆母(PB)细胞和浆细胞,IL-6炎症因子进一步导致血脑屏障及血眼屏障通透性改变、细胞旁路结构和功能的破坏,与此同时致病性抗体、效应细胞、炎症因子、趋化因子在中枢神经系统中攻击星形胶质细胞,受损后进一步大量分泌IL-6,使中枢内胶质细胞、神经元与炎症细胞之间通过cross-talk形成炎症环路,其中IL-6作为炎症放大器显著增强中枢神经系统炎症反应。靶向IL-6通路可抑制NMOSD炎症级联反应,因此萨特利珠单抗可为这类NMOSD患者带来明显治疗获益。
专家述评
NMOSD具有高复发性、高致残性,且每一次复发都会带来残疾累积,因此,预防复发至关重要。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目前NMOSD已有多种序贯治疗药物用于临床,但不同药物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因此,如何基于患者个体特征,尤其是对既往治疗药物无应答时,及时进行药物转换并制定精准的治疗策略,仍是亟待解决的临床难题。在药物转换方面,在2023年发布的《基于德尔菲法的AQP4抗体阳性NMOSD治疗国际共识》中已明确建议,如患者对既往维持治疗药物无应答,临床医生应更换为另一种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进行治疗[8]。
本例患者在接受萨特利珠单抗治疗后,尽管AQP4抗体仍然较高,但患者病情稳定,淋巴细胞亚群基本恢复至正常水平,且用药期间无明显感染及不良反应,表明萨特利珠单抗兼具疗效与安全性。这提示,当NMOSD患者体内B细胞维持低水平但仍然反复发作时,及时转换至不同靶点的生物制剂可能是突破治疗瓶颈的有效策略。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免疫细胞向中枢神经系统的浸润,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内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的活化,普遍存在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中。尽管初期炎症反应对清除威胁、修复损伤具有积极意义,但后期的破坏性效应往往加速神经退行性变,这表明神经免疫与炎症可能是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共同的病理生理机制[9]。
这一理论突破与神经免疫序贯治疗策略高度契合,即通过控制炎症或致病成分、消除致病性免疫记忆细胞以重置免疫系统、促进并维持免疫稳态这三个步骤,帮助NMOSD等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疾病患者获得更佳临床结局[10]。
专家简介

曹树刚 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安徽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安徽省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分会神经免疫学组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神经免疫病(NMOSD、MOGAD、GFAP-A、MG、自免脑等)
调研问题
参考文献:
[1]黄德晖, 吴卫平, 胡学强. 中国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诊断与治疗指南(2021版)[J]. 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 2021,28(06):423-436.
[2]李鸿艳, 王侃, 俞昊君, 等.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的疾病修饰治疗研究进展 [J] .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23, 56(12) : 1435-1446.
[3]侯金花, 章海涛. 长寿命浆细胞与系统性红斑狼疮[J]. 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 2013,22(06):549-553.
[4] Hunter CA, Jones SA. IL-6 as a keystone cytokine in health and disease[J]. Nat Immunol. 2015 May;16(5):448-57.
[5]Liew, Pei. (2012). The Longevity of the Humoral Immune Response: Survival of Long-lived Plasma Cells[J]. Akademeia. 2. ea0116.
[6]Zhang C, Zhang TX, Liu Y, Jia D, Zeng P, Du C, Yuan M, Liu Q, Wang Y, Shi FD. B-Cell Compartmental Features and Molecular Basis for Therapy in Autoimmune Disease[J]. Neurol Neuroimmunol Neuroinflamm. 2021 Aug 31;8(6):e1070.
[7]王玉鸽, 邱伟, 胡学强. 萨特利珠单抗治疗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的研究进展[J]. 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 2021,28(05):411-414.
[8]Paul F, Marignier R, Palace J, et al. International Delphi Consensus on the Management of AQP4-IgG+ NMOSD: Recommendations for Eculizumab, Inebilizumab, and Satralizumab[J]. Neurol Neuroimmunol Neuroinflamm, 2023,10(4).
[9]Shi FD, Yong VW. Neuroinflammation across neurological diseases. Science. 2025 Jun 19;388(6753):eadx0043.
[10] Ramírez-Valle F, et al. Nat Rev Drug Discov. 2024 Jul;23(7):501-524.
*此文仅用于向医学人士提供科学信息,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利鸿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